-
网站首页
- 靖霖推荐
-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司法认定标准及其变迁
前言
经济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必备特征之一(其他三个特征为: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征。对此,笔者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黑帽”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已做详细介绍,在此不追。该文于2019年1月5日发表在“有效辩护”订阅号上,有情趣的读者可以前往阅读),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组织的重要标志。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实质是摸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家底,核心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钱袋子”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通俗地说,就是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1、一个犯罪组织究竟拥有多少钱才算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此为定量分析,也可谓统计结果。2、哪些钱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钱?此为定性分析,也可谓统计口径。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定性是定量的必要前提,定量是定性的必然结果。1997年《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创设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只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这也是所有犯罪的必备特征),未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经济特征并不是本罪的法定构成要素。因此,当年审理涉黑案件,并不需要考虑涉案犯罪组织的钱多钱少问题。后来的“打黑”实践表明,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都很有钱,“有钱”几乎就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代名词。因此,如何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有钱”,自然就成为立法者、司法者不得不思考的大问题。2000年最高法《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首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当具备四个特征,并将其中的经济特征界定为: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据此,“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成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有钱”的司法认定标准。从此,在审理涉黑案件时,要认定涉案犯罪组织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就应当证明该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至于“一定的经济实力”究竟是指多少钱,该《司法解释》并无规定,完全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自由裁量。在吸收司法解释成果的基础上,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四个特征,并将其中的经济特征界定为: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可见,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同样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有钱”的衡量标准,但同样没有回答“一定的经济实力”究竟是指多少钱这一司法实务问题。2006年发起“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后,立法者、司法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认识也不断深入。针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问题,2009年两高一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重申:一定的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成势、称霸一方的基础。但同时指出,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业的利润空间均存在很大差异,加之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发展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因此在办案时不能一般性地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必须达到特定规模或特定数额。本文称之为“特定数额不要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三条对1997年《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作出修正时,完整吸收了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的规定。从此,“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从司法解释上升到立法解释,再从立法解释上升到法律规定,最终成为衡量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有钱”的法定标准。尽管如此,“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表述仍然有失宽泛,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立法总是相对滞后的,而司法是最活跃的法律实践活动,因此,司法者对现实的观照和反应总是比立法者更迅速。2015年最高法《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首次对“一定的经济实力”作出正面回应和解释: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获取的、足以支持该组织运行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经济利益,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组织成员个人掌控也应当计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但这种解释还是没能回答“一定的经济实力”究竟是指多少钱的这一老大难问题。为此,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进一步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应具有的“经济实力”在20-50万元幅度内自行划定—般掌握的最低数额标准。这是自1997《刑法》创设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来,司法机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一定的经济实力”明确规定了最低数额标准,正面回答了长期困扰司法实务界的老大难问题,使“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了一个较为统一、明确、具体的数额标准。本文称之为“具体数额必要说”。当然,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额标准。“打黑”实践表明,对于真正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来说,区区20-50万元实在是九牛一毛。但依然聊胜于无。2018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再次对“一定的经济实力”作出回应和解释: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得一定数量的经济利益,应当认定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包括调动一定规模的经济资源用以支持该组织活动的能力。通过上述方式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组织成员个人掌控,也应计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该《指导意见》用“一定数量的经济利益”去解释“一定的经济实力”,实为同义反复,并未正面回答“一定的经济实力”究竟是指多少钱的问题。同时,该《指导意见》还首次将“调动一定规模的经济资源用以支持该组织活动的能力”规定为“一定的经济实力”的组成部分,将“能力”视为“经济实力”,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认定“一定的经济实力”的门槛。对于多少钱才算“有钱”的问题,该《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不能一般性地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必须达到特定规模或特定数额。这实际上否定了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的“具体数额必要说”,重新采用了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的“具体数额不要说”。本节小结:“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有钱”的法定标准。对“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司法认知经历了一个从“具体数额不要说”到“具体数额必要说”、又从“具体数额必要说”回归到“具体数额不要说”的变迁过程,可谓从否定到肯定再到否定。从立法(广义上的)的这种反复,明显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立法意趣:“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不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多多益善,上不封顶,少少也可,下不兜底。在笔者看来,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上是逐利性犯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本质上是图利型犯罪。因此,给“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确定一个相对明确的最低数额标准,是合理的,一来可以抑制司法认定的随意性,二来可以凸显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而且,这个最低数额标准还不能定得太低,否则,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就显得不那么有特征了。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的定性标准,通俗地说,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哪些钱(“钱”指代各种形式的财产)可以或者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钱?或者说,哪些钱可以或者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所得(进而装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钱袋子”)?对此,立法者和司法者紧紧围绕“手段”和“用途”两个要素去确立相关的司法认定标准。“手段标准”回答了“钱来何处”问题,“用途标准”回答了“钱用何处”问题。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界定为: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一规定的前半段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率先确立了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钱的“手段标准”。据此,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以下手段获取的钱,都可以认定为该组织的钱,或者说,都可以认定为该组织违法犯罪所得:1、违法活动,2、犯罪活动,3、其他手段。其中,通过违法活动或犯罪活动获取的钱,《刑法》称之为“违法犯罪所得”。这与其他犯罪的违法犯罪所得的规定并无二致,完全符合《刑法》的规定,不会引起任何争议。但该《司法解释》将“其他手段”与“违法活动”、“犯罪活动”相提并论、等同视之,无疑是将“其他手段所得”与“违法犯罪所得”相提并论、等同视之,进而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手段所得”认定为“违法犯罪所得”。这显然突破了《刑法》关于违法犯罪所得的规定,因为在刑法的语境下,除了违法手段、犯罪手段,“其他手段”就只剩下合法手段了。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只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的钱,都属于其违法犯罪所得,至于其获取手段是非法还是合法,则在所不问。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界定为: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据此,该《立法解释》基本确认了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确立的“手段标准”,但也做了部分修正,给“手段标准”增加了“组织性”要素。所谓“组织性”,显然是指以组织的名义、通过组织的行为去获取经济利益且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归组织支配。同时,该《立法解释》首次确立了“用途标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钱应当“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换句话说,只要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的钱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这些钱就可以认定为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所得,至于这些钱是全部用于还是部分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则在所不问。这就是“以商养黑”这一提法的渊源。虽然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和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确立了“手段标准”和“用途标准”,但都还过于原则,还不能完全满足“打黑”司法实践的要求。同时,对于“手段标准”,也还存在一些是否符合《刑法》的质疑声音。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澄清。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率先对“手段标准”中的“其他手段”和“用途标准”中的“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作出明确回应和解释,并且首次明确使用了“以商养黑”、“以黑养商”这二个概念: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敛财方式具有多样性,不仅会通过实施赌博、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而且还往往会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因此,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还是通过合法方式获取,只要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即可。可见,该《座谈会纪要》明确无误地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既包括非法手段,也包括合法手段,不遮掩,不回避,一锤定音地解决了“其他手段”是指非法手段还是合法手段的问题。据此,只要将获取的钱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这些钱就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所得,至于手段是非法还是合法,则在所不问。可见,该《座谈会纪要》不但沿用了“手段标准”和“用途标准”,而且将“用途标准”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所得的最终落脚点,将“用途”拆分成“部分使用”和“全部使用”,只要“部分使用”即满足了“用途标准”的要求。该《座谈会纪要》不但与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和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一脉相承,而且更加清晰无误。虽然解决了“部分使用”和“全部使用”的问题,但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所得的最终落脚点,“用途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为此,该《座谈会纪要》将“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解释为“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并明确规定以下五类费用支出应当认定为“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1、购买作案工具、提供作案经费,2、为受伤、死亡的组织成员提供医疗费、丧葬费,3、为组织成员及其家属提供工资、奖励、福利、生活费用,4、为组织寻求非法保护支出的费用,5、其他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费用支出。沿着“手段标准”和“用途标准”的路径,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明确将以下三类资产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资产:1、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资产,2、有组织地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资产,3、组织成员以及其他单位、个人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资产。这一规定基本囊括了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任何手段、通过任何途径、从任何人获取的任何资产,基本封杀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所有“财路”,包括首次规定的“资助”通道,可谓一网打尽。同时,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还对“用途标准”进行了细化和补缺,明确规定,是否将所获经济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的重要依据,无论获利后的分配与使用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在客观上能够起到豢养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壮大组织势力的作用,即满足了“用途标准”要求,即可认定为“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最新的配套司法文件,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对“手段标准”进行了归纳总结,明确规定:在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通过以下方式获取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1、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2、有组织地以投资、控股、参股、合伙等方式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3、由组织成员提供或通过其他单位、组织、个人资助取得。尽管措词有所不同,但其精神意蕴与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完全一致。《指导意见》还首次规定:组织成员主动将个人或者家庭资产中的一部分用以支持该组织活动,其个人或者家庭资产可全部计入“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数额明显较小或仅提供动产、不动产使用权的除外。本节小结: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钱,不问来源何处,不问合法与否,只要同时满足了“手段标准”和“用途标准”,就可以乃至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所得(接下来当然是面临被追缴、没收的命运),严厉程度可谓无以复加,充分体现了要彻底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以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要釜底抽薪、连根拔起的刑事政策目标。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摸清黑社会性质组织“家底”的过程,微观上是为了满足“入罪”条件,宏观上则是为追缴、没收做准备。但追缴、没收只具有“剥夺剥夺的”的功能,因为其对象只限于违法犯罪所得。上文论及的“手段标准”,将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开办公司企业、投资、控股、参股、合伙等合法方式取得的财产认定为违法犯罪所得,进而可以作为追缴、没收的对象,目的当然是尽可能扩大追缴、没收的财产范围。但这种制度设计的法律逻辑是“坏人做坏事”,与“对事不对人”的现代刑法理念相悖,还有与《刑法》相抵触之嫌。事实上,要实现彻底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的政策目标,除了借助追缴、没收这两种刑事司法措施外,还可以借助财产刑,因为财产刑具有“剥夺剥夺者”的功能。对此,笔者近期将撰文探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财产刑,有兴趣的读者届时可以跟踪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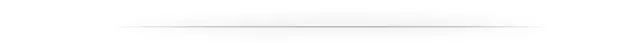
靖霖(武汉)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7月4日获批成立,系靖霖在华中地区设立的一家专门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律所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金融中心地段的中北路海山金谷12楼,毗邻汉街商圈,可远眺东湖,办公面积1200余平。 目前有专业律师20余名专门从事刑事业务,其中半数以上具有公检法工作经历。靖霖律师秉承“攻刑以专,相靖以霖”的所训,依托武汉地区众多高校与文化资源,与靖霖总部及各分所形成合力,着重加强刑事业务的实践与研究,将靖霖的法律服务理念及产品进一步推广。同时,致力于打造一支刑辩专业队伍,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兢业的法律服务,为推进武汉刑事法律业务专业化发展贡献力量。
上海:黄浦区中山东二路88号外滩SOHOC座19层杭州:滨江区江南大道4760号亚科中心B座15、16层
贵阳:观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金融中心14号楼15层济南:历下区经十路9777号鲁商国奥城4号楼15层昆明:滇池路569号南亚风情第壹城国际B座19层1903天津:红桥区北马路170号陆家嘴金融广场A座39层福州:台江区宁化街宁化街道振武路70号福晟钱隆广场34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