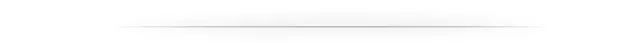-
网站首页
- 靖霖推荐
-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司法认定标准
本文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黑帽”是怎样炼成的?》(2019年1月5日发表在“有效辩护”订阅号)的续篇,集中梳理了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十个司法认定标准。笔者将于近期分别就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征的司法认定标准进行逐一梳理,以期帮助读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必备特征建立起系统、完整的认识。第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概念及内涵。
组织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组织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被置于其四个必备特征之首,本文称之为“组织帽”。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帽”并非原本就有,而是与“打黑”司法实践紧密相关、相互相成,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疏到密的制度变迁过程。一、1997年《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创设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一罪名,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类人”——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但没有明确使用“骨干分子”和“组织特征”这二个概念。从罪刑法定的角度看,那时,组织特征还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不属于本罪的法定构成要素。二、2000年最高法《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首次引入“骨干分子”和“组织特征”这二个概念,并初步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内涵: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据此,只有同时具备五个条件,涉案犯罪组织才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2、人数较多,3、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4、骨干成员基本固定,5、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三、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沿用了“组织特征”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内涵: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据此,只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涉案犯罪组织就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2、人数较多,3、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4、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内涵,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和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都要求人数较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这是二者的相同点,但也存在显著区别:1、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对组织特征只提出“紧密性”要求,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则提出了“稳定性”要求。在笔者看来,“紧密性”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管理关系,即存续状态,“稳定性”则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命周期,即存续时间。“稳定性”与“紧密性”大体上是包含关系,“稳定性”包含了“紧密性”。可见,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对组织特征规定了更高的标准。2、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领导者,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采用“比较明确”标准,弹性较大;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则采用“明确”标准,弹性较小,从而限缩了组织者、领导者的范围。3、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应“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则没有这一要求。“打黑”实践表明,“组织纪律”的有无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组织的重要标志,与其“稳定性”密切相关。四、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三条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修正时,最终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内涵: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至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从无到有,从司法解释上升到立法解释,再从立法解释上升到法律规定,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法定特征之一。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不断地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特征的内涵进行解释,从以下十个主要范畴逐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内涵和外延,确立了其司法认定标准,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从抽象变得具体,成为可以被证明的对象,以回应“打黑”和“扫黑”实践的需求。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的司法认定标准:从空白标准到主观标准再到客观标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是涉黑案件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它不但直接影响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人数、组织犯罪的范围、组织财产的范围,而且直接影响到组织者、领导者的刑事责任范围。因此,根据一定的标准去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稳定性”,即应当存续一定的时间。存续,就意味着必须有“始”有“终”。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始”于何时,就成为涉黑案件中一个必须予以证明的事实。2009年两高一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不宜作出“一刀切”的规定。对于那些已存在一定时间并且成员人数较多的犯罪组织,在定性时要根据其是否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否已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等情况综合分析判断。可见,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并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作出明确规定,只要求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时间与其经济特征、危害性特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即只提出了一个“综合判断标准”。由于这一标准过于弹性,实践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就可能一直提前到1997年,因为这是这一罪名的创设元年。2015年最高法《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首次就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提出了客观认定标准:(1)“成立仪式”标准。可以根据涉案犯罪组织举行成立仪式或进行类似活动的时间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2)“重大事件”标准。如果不存在前一个标准,则可以根据足以反映涉案犯罪组织初步形成核心利益或强势地位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来审査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3)“首次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标准。如果不存在前二个标准,则可以根据以下二个时间点来审查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①涉案犯罪组织为维护、扩大其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而首次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时间,或②涉案犯罪组织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首次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时间(说明:这一标准要求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既不包括有组织的违法活动,也不包括组织成员的个人犯罪活动)。至于如何认定“首次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需要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的司法认定标准来审查判断。对此,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再做详细说明,在此不赘。2018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重申了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不宜“一刀切”的规定,并调整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时间的客观认定标准,成为目前的最新标准。 (1)“成立仪式”标准。与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完全相同。(2)“标志性事件”标准。如果不存在前一个标准,可以按照足以反映涉案犯罪组织初步形成非法影响的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时间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3)“首次共同实施组织犯罪活动”标准。如果不存在前二个标准,可以将组织者、领导者与其他组织成员首次共同实施该组织犯罪活动的时间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即使组织者、领导者因未到案或因死亡等法定情形未被起诉也不影响认定。至于如何认定“首次共同实施组织犯罪活动”,需要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的司法认定标准来审查判断。对此,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再做详细说明,在此不赘。“打早打小”和“打准打实”是“打黑”和“扫黑”的既定方针,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密切相关。那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人数应否有一个最低标准呢?对此,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和《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都只规定了“人数较多”的原则性标准,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则认为不宜作出“一刀切”规定。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首次对“人数较多”作出明确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有一定规模,组织成员一般在10人以上。这就是“十人标准”。既然有了具体的人数标准,就必须有相应的统计口径。为此,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还首次明确了组织成员人数的统计口径:既包括被起诉的组织成员,也包括未归案的、因法定事由未被起诉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的组织成员。但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确立的“十人标准”只实施了三年时间。“扫黑打恶”专项斗争启动后,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重申了不宜“一刀切”规定,实际上否定了“十人标准”。因此,自2018年起,如果成员人数超过三人,涉案犯罪组织就有可能被升格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的司法认定标准。不论是“打黑”还是“扫黑”,打击锋芒始终直指组织者、领导者。一旦被认定为组织者、领导者,基本上就意味着灭顶之灾: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个人财产可能被全部没收,在自首、立功、量刑、取保、减刑、假释等方面均从严掌握,而且实行跨省异地服刑。那么,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呢?对此,《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均无规定。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首次对组织者、领导者作出明确解释:组织者、领导者,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起者、创建者,或在组织中实际处于领导地位、对整个组织及其运行、活动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的犯罪分子,既包括通过一定形式产生的有明确职务、称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包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被公认的事实上的组织者、领导者。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了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标准:发起、创建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合并、分立、重组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实际对整个组织的发展、运行、活动进行决策、指挥、协调、管理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既包括通过一定形式产生的有明确职务、称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包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被公认的事实上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定构成要素,也是其“稳定性”的重要标志,即骨干成员的有无及多寡,是一项必须予以证明的事实。因此,认定若干骨干成员并据此认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就成为所有“入罪”的涉黑案件判决中的必备内容。那么,哪些人可以被认定为骨干分子呢?在本文提及的法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中,只有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唯一一次对“骨干成员”作出了明确的解释:骨干成员,是指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并多次指挥或积极参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长时间在犯罪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属于积极参加者的一部分。据此,骨干成员首先必须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同时还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2、多次指挥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多次积极参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长时间在犯罪组织中起重要作用。与骨干成员不同,积极参加者不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类法定成员之一,而且还有独立的法定刑。因此,根据一定的标准来认定积极参加者,就成为“打黑”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但事实上,从1997年到2009年的十二年间,一直没有针对积极参加者的司法认定标准。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首次对积极参加者作出明确规定:积极参加者,是指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如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管理等事项的犯罪分子。据此,只要接受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成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并且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之一,就可以被认定为积极参加者:1、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多次,应当是三次以上。积极,是对“多次”的评价。所参与的,既可以是违法活动,也可以是犯罪活动,但必须是“组织的”违法活动或者犯罪活动,不包括个人的违法活动或犯罪活动,至于违法活动或犯罪活动是否严重,则在所不问),2、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没有参与次数要求,参与一次即可。所参与的,必须是较严重的犯罪活动,而且必须是“组织的”犯罪活动,既不包括“组织的”违法活动,也不包括个人的犯罪活动。作用突出,是指起主要作用,即在本次犯罪活动中可以被评价为主犯),3、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如具体主管财务或人员管理等事项(这是认定积极参加者的兜底条款,即使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只要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主管财务、人员管理等事项,就被认为在组织中起了重要作用,就可以被认定为积极参加者)。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再次重申了积极参加者的司法认定标准: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情形,如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管理等事项。从表面上看,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与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基本一致,没有创设新的标准,但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规定,只要符合积极参加者的三个条件之一,就“一般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者,从而限制了司法裁量权。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比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更加严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参加者,也叫其他参加者。在2009年之前,一直没有针对一般参加者的统一司法认定标准,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边界模糊不清,导致“打黑”实践中扩大化或缩小化的倾向。为填补这一法律空白,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规定,其他参加者是指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积极参加者以外的、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的犯罪分子。这是法律、司法解释唯一一次对一般参加者下定义,从而确立了一般参加者的司法认定标准。当然,这不但是一个门槛很低的标准,而且容易产生歧义,例如,如何认定“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涉黑案件中,只要参加过一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就可能被认定为“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进而可能被认定为一般参加者:1、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仪式或类似活动,2、出席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会议或集会,3、相对固定地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企业工作并领取固定或不固定的工资或其他福利,4、给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过资金或活动场所。除组织者和领导者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参加者”,只不过是在参加者又分为一般参加者和积极参加者,积极参加者又分为骨干成员和非骨干成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属于故意犯罪行为,过失不构成本罪。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被告人必须同时具备“参加”的主观故意和“参加”的客观行为,才能被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二者缺一不可。不管是骨干成员、积极参加者还是一般参加者,都存在如何认定其“参加”的主观故意和“参加”的客观行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涉黑案件中,被指控为骨干成员、积极参加者或一般参加者的被告人,基本上都会提出这样的抗辩:我根本就不知道存在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怎么能指控我参加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呢?这种抗辩完全有道理,在法律上也完全站得住脚:不知者不罪。这既是普世观念,也是认定故意犯罪的基本原则。既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故意犯罪,如果只能证明其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客观行为,不能证明其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就不应当认定被告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如果勉强认定,就有霸王硬上弓之嫌,既不能令被告人口服心服,也无法服众。因此,确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的主观明知的的司法认定标准就成为必然。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时,并不要求其主观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这是一个“可以认定”标准:符合规定情形的,既可以认定,也可以不认定,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据此,如果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参加的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并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组织,就可以同时认定其具有“参加”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就可以认定其“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至于其在“参加”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组织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则在所不问。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再次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仍加入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是一个“应当认定”标准:只要符合规定情形,就应当认定,法官没有自由裁量权。据此,只要符合以下二个要件,就应当认定被告人“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1、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2、客观上加入该组织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刑法》第第二百九十四条没有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组织纪律。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组织纪律”并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定构成要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组织纪律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稳定性”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黑社会性质组织才可能稳定存续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组织纪律的有无就成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首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没有确立具体的司法认定标准。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再次指出:在通常情况下,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一般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纪律、规约,有些甚至还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具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也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可见,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把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其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在认定组织特征时就应当特别谨慎,甚至“手下留情”。但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依然没有确立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的司法认定标准。时隔六年后,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才有了统一的司法认定标准。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指出: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应当结合制定、形成相关纪律、规约的目的与意图来进行审查判断:凡是为了增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性、隐蔽性而制定或自发形成,并用以明确组织内部人员管理、职责分工、行为规范、利益分配、行动准则等事项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约定,均可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这是针对组织纪律、活动规约的唯一一个司法认定标准。据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的司法认定过程如下:有证据证实存在相关纪律、规约(存在性)→有证据证实制定或自发形成相关纪律、规约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性、隐蔽性(目的性)→有证据证实相关纪律、规约实际应用于组织内部人员管理、职责分工、行为规范、利益分配、行动准则等事项(应用性)→相关纪律、规约就可以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结论)。可见,只要同时符合存在性、目的性和应用性的要求,相关纪律、规约就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至于是制定的还是自发形成的,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则在所不问。涉黑案件往往牵涉人数众多,动辄几十人。在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中,如果指控、认定所有涉案人员都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送进监狱,既无必要,监狱恐怕也难于承受;在涉案人员较少的案件中,如果不尽可能多地把涉案人员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成员人数就可能太少,其组织特征可能就不明显、甚至不能认定。为化解这一矛盾,同时又达到打击少数、教育多数的目的,2000年最高法《司法解释》和2009年两高一部《座谈会纪要》均规定,以下两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1、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后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2、因受蒙蔽、胁迫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且情节轻微。在此基础上,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增加了一类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参加者: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后仅参与少量情节轻微的违法活动。此处所指“不作为犯罪处理”,是指不作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理,即不指控或不认定其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涉黑案件往往涉及数量庞大的外围人员,他们都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对这些外围人员应当如何处理呢?对此,在2015年之前一直没有统一规定,在个案中完全由司法人员作出判断和处理。2015年最高法《座谈会纪要》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明确规定以下三类人员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1、主观上没有加入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或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2、因临时被纠集、雇佣、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3、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佣、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再次重申: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应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本文梳理了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的十个司法认定标准。其中前八个是认定标准,可称之为“入罪”标准,后二个是排除标准,可称之为“出罪”标准。只有全面透彻地了解这些司法认定标准,才能在涉黑案件中提出有的放矢的辩护观点,有效辩护才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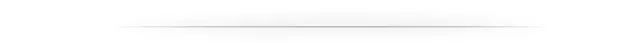
联系电话|17771897872 、02787363402点击此文字查看靖霖武汉所招聘详细信息
靖霖(武汉)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7月4日获批成立,系靖霖在华中地区设立的一家专门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律所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金融中心地段的中北路海山金谷12楼,毗邻汉街商圈,可远眺东湖,办公面积1200余平。 目前有专业律师20余名专门从事刑事业务,其中半数以上具有公检法工作经历。靖霖律师秉承“攻刑以专,相靖以霖”的所训,依托武汉地区众多高校与文化资源,与靖霖总部及各分所形成合力,着重加强刑事业务的实践与研究,将靖霖的法律服务理念及产品进一步推广。同时,致力于打造一支刑辩专业队伍,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兢业的法律服务,为推进武汉刑事法律业务专业化发展贡献力量。
上海:黄浦区中山东二路88号外滩SOHOC座19层杭州:滨江区江南大道4760号亚科中心B座15、16层
贵阳:观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金融中心14号楼15层济南:历下区经十路9777号鲁商国奥城4号楼15层昆明:滇池路569号南亚风情第壹城国际B座19层1903天津:红桥区北马路170号陆家嘴金融广场A座39层福州:台江区宁化街宁化街道振武路70号福晟钱隆广场34层